
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全文如下:
情真意切 涓涓流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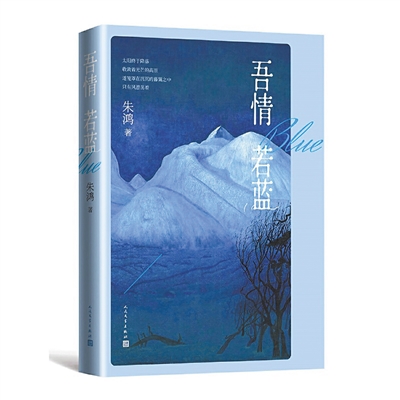
作者:张聪
朱鸿散文集《吾情若蓝》用精练优美的语言,将“在心尖上跳动着爱情、亲情、乡情和大地之情”真切地传递出来,触碰读者内心深处的柔软。书名中的“蓝”是“大海的颜色,长天的颜色”,大海般纯净辽阔、天空般浩瀚深邃的蓝色不仅唤起作者内心深沉的情感,也给读者以精神的慰藉和关怀。
散文集《吾情若蓝》精心挑选了作者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。作者将思绪诉诸笔端,有体验人生的哲理感怀,有抒写真情的心灵独白。读者循着作者的文字,可走进富于诗意的文学世界。《好感》中记述了几位赠予“我”善意的陌生人:宽厚的三轮车司机解“我”燃眉之急,萍水相逢的兄长为“我”雪中送炭,他们的善良维护了“我”的尊严,让“我”感念30余年。由此,“我”得到“小善可以处处做,不以小善而止之”的感悟。《陈忠实先生》《路遥纪念》《独行》《出城踏雪》等篇章,通过回忆与文化名家的交往细节,在抒发作者怀念之情的同时,充分展现这些作家艺术家敦厚高尚的品格。
散文集叙写情感的篇章朴实无华,真诚恳切。《母爱如流》讲述家中三代女性对家庭无私的爱与奉献。“我”的祖母一辈子生活在乡村,去村头等待儿子是她活动范围的极限,但祖母却能够在黑夜里通过“自行车颠簸的声响辨别出是否是儿子平安归来”;“我”的母亲也是一位乡村妇女,她文化水平虽然不高,但却深知读书求学的重要性,每日清晨喊“我”起床读书,“轻轻地,一遍遍地呼唤我,既怕我醒不来,又怕我睡不足”;“我”的妻子是一名现代女性,她的科学育儿观贯穿养育孩子的每个环节。三位母亲对孩子的爱像涓涓细流,流淌在平凡生活的缝隙之中,而这种源于生命本性的爱又是那样不同寻常,如日光、似春雨,给人以勇气和力量。《一次没有表白的爱》《爱之路》等篇章,书写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不落俗套,富有哲理。在《萧关》一文中,“我”搭上一辆班车,开始了充满冒险的行程,虽然旅途费尽周折,但通过作者生动描述,读者在阅读时有着极为真实的在场感。还有《少陵原》《故乡难言》《秦地古镇》《白原》《终南山》等散文,表现了作者无法割舍的乡土情怀。作者用深情的目光打量着这片充满希望与爱的土地,写故土的山川、河流、风土人情,大量的历史地理、人物活动以富有感情和文采的笔触串联起来,引领读者跟随他的步伐,去追寻秦川渭水的历史与当下。
散文集文风清新、娓娓道来。作品写景:“辋川的雨是明净的,线似的,一根一根拉到峡谷,但雨却空得无声无息。”通过以物观物的描写拓展了叙述空间,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氛围;作品状物:“祁坪村有数户人家,房矮墙低,羊走鸡鸣。千山万壑,白云在天”。寥寥几笔,就将板正与风趣、精细与豪放融合在一起。作者在后记里讲述了选文的经过,同时也表达了由于作品比较多,归类和排序只不过是勉强所分的遗憾。这同时也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,散文内容多样,不同章节之间关联不大,这或许与文章结集出版的方式有关。
报道链接: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rmrb/html/2022-04/26/nw.D110000renmrb_20220426_3-20.htm
《光明日报》报道全文如下:
“情”是散文的心
——读散文集《吾情若蓝》
作者:李跃力 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04月20日 14版)
《吾情若蓝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)是朱鸿自编的散文集。作家自编文集之举源远流长,已构成一种文学传统。“自编”并非随意为之,反而更考验作家的眼光、功力与文学观念,它也是一种创造。对朱鸿而言,《吾情若蓝》的编选意义非凡。借此契机,他不仅将几十年来的散文择取连缀,整体性凸显散文创作中“情”的主体地位;而且系统阐发了对散文文体的理解:“散文是兼容审美之质、智慧之光和人格意象于一体的文学形式。它可以自由地叙事、议论和抒情。这一切都应该发乎包括对写作者自己在内的整个生存系统的至诚、敏锐、深刻、准确和独特的感受。”
在《吾情若蓝》中,“情”字一以贯之。整部作品朱鸿列为六个专辑,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亦有思古之幽情,发愤之豪情,内容涉及自我、亲人、爱人、故乡、文化与历史,虽包罗万象,但无不灌注“真”情。朱鸿将这“情”具象化为“蓝”,这不仅是大海长空的颜色,更显示宇宙的浩瀚深邃。吾情若蓝,纯粹澄澈,雄浑博大,永生永恒。
《吾情若蓝》对“情主体”的推崇或有源头。中国文学的“抒情传统”未曾断绝,自屈子“发愤以抒情”至沈从文“抽象的抒情”,“情”一直不断触动作家的文思。“情”绝非置身事外,反而是纵身其中,彰显儒家的现世关怀。朱鸿“向往乡野”“喜欢小麦”,《少陵原》反思城市化的弊病,《咸阳原和五陵原》旗帜鲜明批判功利主义,《曲江萧瑟》告诫人类不要打乱自然的秩序……这“情”不是个人天地中的浅吟低唱,而是直面现实的警世之音,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,也和西方浪漫主义深度对话。
朱鸿并未陈陈相因,其“情”根深植于少陵原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。“长安朱鸿,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。”少陵原不仅是朱鸿念兹在兹的精神原乡,也是匠心独运的文化身份。少陵原是自然之乡、文化之原,它赋予朱鸿一种独特的人格与视野,一种难得的自信与底气。他说:“我是一个出生在少陵原上的人,我见惯了天。”“吾辈降临于这个世界,就生活在自然之中,大地的形势与星空的深邃,是看见了,听见了,而且把对自然的感受永久地留在了灵敏的手指上和脚掌里……”《吾情若蓝》中的人格意象颇具君子之风,又不迂腐呆滞,而是磊落光明、坦坦荡荡、敢爱敢恨,有蛮性与血性存焉。这样的人格意象所抒之“情”,当然充盈着力量,元气淋漓。
朱鸿追求语言的“玉帛之感”,主张“字里行间,应该涌动一种气息”,这与其“情”的不竭能量相得益彰。这种对语言质感与力感的精心营构,与沈从文所言的“韧性”与“硬性”异曲同工。如《母亲的意象》中,“我”在乡间小路迎接迟迟不归的母亲,“终于月悬秦岭,星辰灿烂,母亲像一个漂移的点似的在白杨萧萧的小路上出现了”。其中,“月悬秦岭”“星辰灿烂”“白杨萧萧”,境界阔大清幽,语言短促有力;“漂移的点”又何其渺小,这“情”与“境”激荡人心。朱鸿对语言的“再三推敲”绝非对形式的单纯讲究,而是与“情”表里共生。
郁达夫认为,一篇散文最重要的内容,第一是要寻这“散文的心”。朱鸿编《吾情若蓝》,似可视作寻找“散文的心”的努力,亦可视作为散文立“心”的尝试。这散文的“心”,就是“情”。
(作者:李跃力,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报道链接: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2-04/20/nw.D110000gmrb_20220420_2-14.htm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